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第57节:道德的困境(7)
在 类学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中,这些文化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以耻为主还是以罪为主。更多小说 ltxs520.com根据定义,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
类学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中,这些文化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以耻为主还是以罪为主。更多小说 ltxs520.com根据定义,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 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不过这种社会里的
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不过这种社会里的 ,例如美国
,例如美国 ,在犯了些许过错之后,也会因内疚而有羞耻感。有时因衣着不得体,或者因为言辞有误,都会感到万分懊悔。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
,在犯了些许过错之后,也会因内疚而有羞耻感。有时因衣着不得体,或者因为言辞有误,都会感到万分懊悔。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 们会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犯罪的行为感到懊悔。这种懊悔可能非常强烈,但却不能像罪恶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犯了罪的
们会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犯罪的行为感到懊悔。这种懊悔可能非常强烈,但却不能像罪恶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犯了罪的 可以通过忏悔而减轻内心沉重的负担。忏悔这种手段已运用于世俗世界的心理治疗,许多宗教团体也用它。但是二者在其他方面鲜有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忏悔可以解脱。但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世界,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犯错误的
可以通过忏悔而减轻内心沉重的负担。忏悔这种手段已运用于世俗世界的心理治疗,许多宗教团体也用它。但是二者在其他方面鲜有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忏悔可以解脱。但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世界,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犯错误的 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他会感到只要恶行没有公诸于世就不必懊丧,因为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忏悔的说法,甚至对上帝的忏悔也没有。他们有祈福仪式,却没有赎罪仪式。
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他会感到只要恶行没有公诸于世就不必懊丧,因为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忏悔的说法,甚至对上帝的忏悔也没有。他们有祈福仪式,却没有赎罪仪式。
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的强制力来行善,这和真正的罪感文化借助于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是完全不同的。羞耻是对别 批评的反应。一个
批评的反应。一个 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觉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
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觉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 在场,至少要当事
在场,至少要当事 感觉到有外
感觉到有外 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在有的民族,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在这种
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在有的民族,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在这种 况下,即使恶行未被
况下,即使恶行未被 发觉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感折磨,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
发觉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感折磨,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
早期移居美国的清教徒们曾试图把一切道德置于罪恶感的基础之上,并且所有的 神病学者都知道现代美国
神病学者都知道现代美国 内心有什么苦恼。但在美国,羞耻感正在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而罪恶感则大不如以前那么容易被感觉到了。美国
内心有什么苦恼。但在美国,羞耻感正在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而罪恶感则大不如以前那么容易被感觉到了。美国 把这种现象解读为道德的松懈。这种解释虽然也蕴涵着许多真理,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羞耻感能担起道德的重任。我们不能把伴随耻辱而出现的强烈的个
把这种现象解读为道德的松懈。这种解释虽然也蕴涵着许多真理,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羞耻感能担起道德的重任。我们不能把伴随耻辱而出现的强烈的个 懊恼纳
懊恼纳 我们的基本道德体系。
我们的基本道德体系。
而 本
本 却是把羞耻感纳
却是把羞耻感纳 道德体系的。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准,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偶然
道德体系的。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准,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偶然 的出现都是耻辱。他们认为耻是道德的根本。对耻辱敏感的
的出现都是耻辱。他们认为耻是道德的根本。对耻辱敏感的 就能够实践善行的一切标准。“知耻之
就能够实践善行的一切标准。“知耻之 (amanwhoknowsshame)”就译成“有德之
(amanwhoknowsshame)”就译成“有德之 (virtuousman)”,有时也译成“重名之
(virtuousman)”,有时也译成“重名之 (manofhonour)”。与“纯洁良心”、“笃信上帝”、“避免罪恶”等在西方伦理中的地位一样,耻感在
(manofhonour)”。与“纯洁良心”、“笃信上帝”、“避免罪恶”等在西方伦理中的地位一样,耻感在 本伦理道德中也具有同样的权威地位。以此逻辑推论,
本伦理道德中也具有同样的权威地位。以此逻辑推论, 死之后就不会受到惩罚。除了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外,
死之后就不会受到惩罚。除了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外, 本
本 对那种今生修行,来世有好报的因果
对那种今生修行,来世有好报的因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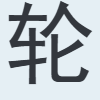 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除少数皈依基督者外,他们也不承认来世报应及天堂地狱惩罚之说。
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除少数皈依基督者外,他们也不承认来世报应及天堂地狱惩罚之说。
正如其他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羞耻感在 本
本 生活中的重要
生活中的重要 也是
也是
 体会得到的。任何
体会得到的。任何 本
本 都对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十分关注。他只需要推测出别
都对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十分关注。他只需要推测出别 做的判断,并针对别
做的判断,并针对别 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当每个
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当每个 都遵守同一规则并相互支持时,
都遵守同一规则并相互支持时, 本
本 就会感到轻松而愉快。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
就会感到轻松而愉快。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 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非常狂热地参加。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
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非常狂热地参加。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 本善行标准的国度时,他们最易受到伤害。他们“善良”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失败了,中国
本善行标准的国度时,他们最易受到伤害。他们“善良”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失败了,中国 和菲律宾
和菲律宾 所采取的态度令许多
所采取的态度令许多 本
本 感到愤慨。
感到愤慨。
那些为了求学或经商到美国的 本
本 并不是受国家主义
并不是受国家主义 绪所驱使的。但是,当他们试图在这个道德规范不那么严格的社会生活时,就常常感到他们过去所接受的那种细致的教育是个“失败”。他们感到
绪所驱使的。但是,当他们试图在这个道德规范不那么严格的社会生活时,就常常感到他们过去所接受的那种细致的教育是个“失败”。他们感到 本的美德不能很好地输出。他们想说明的并不是所谓的改变对任何
本的美德不能很好地输出。他们想说明的并不是所谓的改变对任何 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他们想说的远比这多得多。比起他们所熟知的中国
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他们想说的远比这多得多。比起他们所熟知的中国 、暹罗
、暹罗 来说,
来说, 本
本 适应美国式生活要困难得多。
适应美国式生活要困难得多。 本
本 的特殊问题在于,在他们看来他们是靠这样一个安全感长大的——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
的特殊问题在于,在他们看来他们是靠这样一个安全感长大的——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 承认其微妙的意义。他们看到外国
承认其微妙的意义。他们看到外国 对这类礼节毫不在乎时,就茫然若失。他们千方百计寻找西方
对这类礼节毫不在乎时,就茫然若失。他们千方百计寻找西方 生活中与
生活中与 本
本 类似的细节,一旦找不到,有些
类似的细节,一旦找不到,有些 就感到非常愤慨,有些
就感到非常愤慨,有些 则感到震惊。
则感到震惊。
在其自传《我的狭岛祖国》中2,三岛 士(mishima)成功地描写了她在道德规范不甚严格的文化中的体验,无
士(mishima)成功地描写了她在道德规范不甚严格的文化中的体验,无 能出其右。她是如此渴望到美国留学,她说服了她保守的家
能出其右。她是如此渴望到美国留学,她说服了她保守的家 们“不愿受恩”的观点,接受一个美国奖学金最终进
们“不愿受恩”的观点,接受一个美国奖学金最终进 了卫斯理学院学习。她说,老师和同学都对她特别友善,但这却使她感到更困难。“
了卫斯理学院学习。她说,老师和同学都对她特别友善,但这却使她感到更困难。“ 本
本 的共同特点是以品行无缺陷而自豪,我这种自豪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很生气我自己不知道在这里该怎样恰当行事,而周围的环境却似乎在嘲笑我以前的经验。除了这种模糊而又根
的共同特点是以品行无缺陷而自豪,我这种自豪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很生气我自己不知道在这里该怎样恰当行事,而周围的环境却似乎在嘲笑我以前的经验。除了这种模糊而又根 蒂固的恼恨以外,我心中再也没有其他激
蒂固的恼恨以外,我心中再也没有其他激 。”她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从其他行星上掉下来的
。”她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从其他行星上掉下来的 ,原有的感觉和
,原有的感觉和 感在这个世界都用不上。
感在这个世界都用不上。 本式的教养要求任何动作都要文静优雅,每一句言辞都要礼貌规范,在当前的环境中我十分敏感,以至于在社
本式的教养要求任何动作都要文静优雅,每一句言辞都要礼貌规范,在当前的环境中我十分敏感,以至于在社 活动中茫然不知所措。”二、三年的时间才使她解除了紧张状态,并且开始接受别
活动中茫然不知所措。”二、三年的时间才使她解除了紧张状态,并且开始接受别 的好意。她认为,美国
的好意。她认为,美国 生活在一种她所谓的“优美的亲密感”之中。而“在我三岁时,亲密感就被当作不礼貌而抹杀掉了”。
生活在一种她所谓的“优美的亲密感”之中。而“在我三岁时,亲密感就被当作不礼貌而抹杀掉了”。
三岛 士把她在美国结识的
士把她在美国结识的 本
本 孩子和中国
孩子和中国 孩子做了比较,她认为美国生活对两国姑娘的影响完全不同。中国姑娘具有的“那种沉稳风度和社
孩子做了比较,她认为美国生活对两国姑娘的影响完全不同。中国姑娘具有的“那种沉稳风度和社 能力是大多数
能力是大多数 本姑娘所不具备的。在我看来,这些上流社会中的中国姑娘是世界上最文雅的
本姑娘所不具备的。在我看来,这些上流社会中的中国姑娘是世界上最文雅的 ,她们
,她们
 都具有近乎尊贵的仪表,仿佛她们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
都具有近乎尊贵的仪表,仿佛她们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 。即使在高度机械化与高速度发展的文明中,她们恬静和沉稳的
。即使在高度机械化与高速度发展的文明中,她们恬静和沉稳的 格与
格与 本姑娘的怯懦、拘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显示出一些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
本姑娘的怯懦、拘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显示出一些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
和其他许多 本
本 一样,三岛
一样,三岛 士感到好像网球名将参加槌球游戏,再优秀的技艺也无法表现,因为她的专业技能无法得到发挥。她感到过去所学到的东西是不能够带到新环境中来的。她过去所接受的那些行为准则是无用的,美国
士感到好像网球名将参加槌球游戏,再优秀的技艺也无法表现,因为她的专业技能无法得到发挥。她感到过去所学到的东西是不能够带到新环境中来的。她过去所接受的那些行为准则是无用的,美国 用不着它们。
用不着它们。
一旦 本
本 接受了美国那种不甚烦琐的行为规则,哪怕只接受了一点点,那就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再过
接受了美国那种不甚烦琐的行为规则,哪怕只接受了一点点,那就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再过 本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了。有时,他们把过去的生活说成是“失乐园”;有时又说成是“桎梏”;有时则说成是“监牢”;有时又说成是有小松树的盆栽。只要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这就是一件为花园增添风雅的艺术品;一旦移植到野地上它就不可能再称其为盆栽了。他们感到再也不能成为
本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了。有时,他们把过去的生活说成是“失乐园”;有时又说成是“桎梏”;有时则说成是“监牢”;有时又说成是有小松树的盆栽。只要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这就是一件为花园增添风雅的艺术品;一旦移植到野地上它就不可能再称其为盆栽了。他们感到再也不能成为 本花园的点缀了,再不能适应往
本花园的点缀了,再不能适应往 的要求了。他们以最尖锐的形式经历了
的要求了。他们以最尖锐的形式经历了 本的道德困境。
本的道德困境。
[记住网址 龙腾小说 ltxs520.com]
 类学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中,这些文化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以耻为主还是以罪为主。更多小说 ltxs520.com根据定义,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
类学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中,这些文化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以耻为主还是以罪为主。更多小说 ltxs520.com根据定义,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 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不过这种社会里的
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不过这种社会里的 ,例如美国
,例如美国 ,在犯了些许过错之后,也会因内疚而有羞耻感。有时因衣着不得体,或者因为言辞有误,都会感到万分懊悔。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
,在犯了些许过错之后,也会因内疚而有羞耻感。有时因衣着不得体,或者因为言辞有误,都会感到万分懊悔。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 们会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犯罪的行为感到懊悔。这种懊悔可能非常强烈,但却不能像罪恶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犯了罪的
们会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犯罪的行为感到懊悔。这种懊悔可能非常强烈,但却不能像罪恶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犯了罪的 可以通过忏悔而减轻内心沉重的负担。忏悔这种手段已运用于世俗世界的心理治疗,许多宗教团体也用它。但是二者在其他方面鲜有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忏悔可以解脱。但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世界,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犯错误的
可以通过忏悔而减轻内心沉重的负担。忏悔这种手段已运用于世俗世界的心理治疗,许多宗教团体也用它。但是二者在其他方面鲜有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忏悔可以解脱。但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世界,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犯错误的 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他会感到只要恶行没有公诸于世就不必懊丧,因为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忏悔的说法,甚至对上帝的忏悔也没有。他们有祈福仪式,却没有赎罪仪式。
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他会感到只要恶行没有公诸于世就不必懊丧,因为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忏悔的说法,甚至对上帝的忏悔也没有。他们有祈福仪式,却没有赎罪仪式。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的强制力来行善,这和真正的罪感文化借助于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是完全不同的。羞耻是对别
 批评的反应。一个
批评的反应。一个 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觉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
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觉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 在场,至少要当事
在场,至少要当事 感觉到有外
感觉到有外 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在有的民族,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在这种
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在有的民族,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在这种 况下,即使恶行未被
况下,即使恶行未被 发觉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感折磨,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
发觉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感折磨,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早期移居美国的清教徒们曾试图把一切道德置于罪恶感的基础之上,并且所有的
 神病学者都知道现代美国
神病学者都知道现代美国 内心有什么苦恼。但在美国,羞耻感正在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而罪恶感则大不如以前那么容易被感觉到了。美国
内心有什么苦恼。但在美国,羞耻感正在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而罪恶感则大不如以前那么容易被感觉到了。美国 把这种现象解读为道德的松懈。这种解释虽然也蕴涵着许多真理,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羞耻感能担起道德的重任。我们不能把伴随耻辱而出现的强烈的个
把这种现象解读为道德的松懈。这种解释虽然也蕴涵着许多真理,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羞耻感能担起道德的重任。我们不能把伴随耻辱而出现的强烈的个 懊恼纳
懊恼纳 我们的基本道德体系。
我们的基本道德体系。而
 本
本 却是把羞耻感纳
却是把羞耻感纳 道德体系的。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准,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偶然
道德体系的。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准,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偶然 的出现都是耻辱。他们认为耻是道德的根本。对耻辱敏感的
的出现都是耻辱。他们认为耻是道德的根本。对耻辱敏感的 就能够实践善行的一切标准。“知耻之
就能够实践善行的一切标准。“知耻之 (amanwhoknowsshame)”就译成“有德之
(amanwhoknowsshame)”就译成“有德之 (virtuousman)”,有时也译成“重名之
(virtuousman)”,有时也译成“重名之 (manofhonour)”。与“纯洁良心”、“笃信上帝”、“避免罪恶”等在西方伦理中的地位一样,耻感在
(manofhonour)”。与“纯洁良心”、“笃信上帝”、“避免罪恶”等在西方伦理中的地位一样,耻感在 本伦理道德中也具有同样的权威地位。以此逻辑推论,
本伦理道德中也具有同样的权威地位。以此逻辑推论, 死之后就不会受到惩罚。除了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外,
死之后就不会受到惩罚。除了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外, 本
本 对那种今生修行,来世有好报的因果
对那种今生修行,来世有好报的因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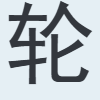 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除少数皈依基督者外,他们也不承认来世报应及天堂地狱惩罚之说。
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除少数皈依基督者外,他们也不承认来世报应及天堂地狱惩罚之说。正如其他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羞耻感在
 本
本 生活中的重要
生活中的重要 也是
也是
 体会得到的。任何
体会得到的。任何 本
本 都对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十分关注。他只需要推测出别
都对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十分关注。他只需要推测出别 做的判断,并针对别
做的判断,并针对别 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当每个
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当每个 都遵守同一规则并相互支持时,
都遵守同一规则并相互支持时, 本
本 就会感到轻松而愉快。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
就会感到轻松而愉快。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 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非常狂热地参加。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
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非常狂热地参加。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 本善行标准的国度时,他们最易受到伤害。他们“善良”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失败了,中国
本善行标准的国度时,他们最易受到伤害。他们“善良”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失败了,中国 和菲律宾
和菲律宾 所采取的态度令许多
所采取的态度令许多 本
本 感到愤慨。
感到愤慨。那些为了求学或经商到美国的
 本
本 并不是受国家主义
并不是受国家主义 绪所驱使的。但是,当他们试图在这个道德规范不那么严格的社会生活时,就常常感到他们过去所接受的那种细致的教育是个“失败”。他们感到
绪所驱使的。但是,当他们试图在这个道德规范不那么严格的社会生活时,就常常感到他们过去所接受的那种细致的教育是个“失败”。他们感到 本的美德不能很好地输出。他们想说明的并不是所谓的改变对任何
本的美德不能很好地输出。他们想说明的并不是所谓的改变对任何 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他们想说的远比这多得多。比起他们所熟知的中国
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他们想说的远比这多得多。比起他们所熟知的中国 、暹罗
、暹罗 来说,
来说, 本
本 适应美国式生活要困难得多。
适应美国式生活要困难得多。 本
本 的特殊问题在于,在他们看来他们是靠这样一个安全感长大的——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
的特殊问题在于,在他们看来他们是靠这样一个安全感长大的——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 承认其微妙的意义。他们看到外国
承认其微妙的意义。他们看到外国 对这类礼节毫不在乎时,就茫然若失。他们千方百计寻找西方
对这类礼节毫不在乎时,就茫然若失。他们千方百计寻找西方 生活中与
生活中与 本
本 类似的细节,一旦找不到,有些
类似的细节,一旦找不到,有些 就感到非常愤慨,有些
就感到非常愤慨,有些 则感到震惊。
则感到震惊。在其自传《我的狭岛祖国》中2,三岛
 士(mishima)成功地描写了她在道德规范不甚严格的文化中的体验,无
士(mishima)成功地描写了她在道德规范不甚严格的文化中的体验,无 能出其右。她是如此渴望到美国留学,她说服了她保守的家
能出其右。她是如此渴望到美国留学,她说服了她保守的家 们“不愿受恩”的观点,接受一个美国奖学金最终进
们“不愿受恩”的观点,接受一个美国奖学金最终进 了卫斯理学院学习。她说,老师和同学都对她特别友善,但这却使她感到更困难。“
了卫斯理学院学习。她说,老师和同学都对她特别友善,但这却使她感到更困难。“ 本
本 的共同特点是以品行无缺陷而自豪,我这种自豪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很生气我自己不知道在这里该怎样恰当行事,而周围的环境却似乎在嘲笑我以前的经验。除了这种模糊而又根
的共同特点是以品行无缺陷而自豪,我这种自豪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很生气我自己不知道在这里该怎样恰当行事,而周围的环境却似乎在嘲笑我以前的经验。除了这种模糊而又根 蒂固的恼恨以外,我心中再也没有其他激
蒂固的恼恨以外,我心中再也没有其他激 。”她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从其他行星上掉下来的
。”她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从其他行星上掉下来的 ,原有的感觉和
,原有的感觉和 感在这个世界都用不上。
感在这个世界都用不上。 本式的教养要求任何动作都要文静优雅,每一句言辞都要礼貌规范,在当前的环境中我十分敏感,以至于在社
本式的教养要求任何动作都要文静优雅,每一句言辞都要礼貌规范,在当前的环境中我十分敏感,以至于在社 活动中茫然不知所措。”二、三年的时间才使她解除了紧张状态,并且开始接受别
活动中茫然不知所措。”二、三年的时间才使她解除了紧张状态,并且开始接受别 的好意。她认为,美国
的好意。她认为,美国 生活在一种她所谓的“优美的亲密感”之中。而“在我三岁时,亲密感就被当作不礼貌而抹杀掉了”。
生活在一种她所谓的“优美的亲密感”之中。而“在我三岁时,亲密感就被当作不礼貌而抹杀掉了”。三岛
 士把她在美国结识的
士把她在美国结识的 本
本 孩子和中国
孩子和中国 孩子做了比较,她认为美国生活对两国姑娘的影响完全不同。中国姑娘具有的“那种沉稳风度和社
孩子做了比较,她认为美国生活对两国姑娘的影响完全不同。中国姑娘具有的“那种沉稳风度和社 能力是大多数
能力是大多数 本姑娘所不具备的。在我看来,这些上流社会中的中国姑娘是世界上最文雅的
本姑娘所不具备的。在我看来,这些上流社会中的中国姑娘是世界上最文雅的 ,她们
,她们
 都具有近乎尊贵的仪表,仿佛她们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
都具有近乎尊贵的仪表,仿佛她们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 。即使在高度机械化与高速度发展的文明中,她们恬静和沉稳的
。即使在高度机械化与高速度发展的文明中,她们恬静和沉稳的 格与
格与 本姑娘的怯懦、拘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显示出一些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
本姑娘的怯懦、拘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显示出一些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和其他许多
 本
本 一样,三岛
一样,三岛 士感到好像网球名将参加槌球游戏,再优秀的技艺也无法表现,因为她的专业技能无法得到发挥。她感到过去所学到的东西是不能够带到新环境中来的。她过去所接受的那些行为准则是无用的,美国
士感到好像网球名将参加槌球游戏,再优秀的技艺也无法表现,因为她的专业技能无法得到发挥。她感到过去所学到的东西是不能够带到新环境中来的。她过去所接受的那些行为准则是无用的,美国 用不着它们。
用不着它们。一旦
 本
本 接受了美国那种不甚烦琐的行为规则,哪怕只接受了一点点,那就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再过
接受了美国那种不甚烦琐的行为规则,哪怕只接受了一点点,那就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再过 本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了。有时,他们把过去的生活说成是“失乐园”;有时又说成是“桎梏”;有时则说成是“监牢”;有时又说成是有小松树的盆栽。只要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这就是一件为花园增添风雅的艺术品;一旦移植到野地上它就不可能再称其为盆栽了。他们感到再也不能成为
本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了。有时,他们把过去的生活说成是“失乐园”;有时又说成是“桎梏”;有时则说成是“监牢”;有时又说成是有小松树的盆栽。只要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这就是一件为花园增添风雅的艺术品;一旦移植到野地上它就不可能再称其为盆栽了。他们感到再也不能成为 本花园的点缀了,再不能适应往
本花园的点缀了,再不能适应往 的要求了。他们以最尖锐的形式经历了
的要求了。他们以最尖锐的形式经历了 本的道德困境。
本的道德困境。[记住网址 龙腾小说 ltxs520.com]
最新地址:m.ltxsdz.com m.ltxsf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