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 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龙腾小说 ltxsba.com这场风
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龙腾小说 ltxsba.com这场风
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 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
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 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
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 质,因为
质,因为
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
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
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 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 个
个 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 告诉我们,说个
告诉我们,说个 坚
坚
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 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
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 是用去做什
是用去做什
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
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
为 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 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
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 方面。他能言善
方面。他能言善
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
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
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
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 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
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
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 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
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
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 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
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
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 之
之 ”,也就
”,也就
是使天下 不得批评政府。
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
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
的方法。中国 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
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
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
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
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 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
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
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 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
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
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
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 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
史台独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
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
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
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 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
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
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
重臣 练有才之士,
练有才之士, 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
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 ,王安石,
,王安石,
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 ,野心大,
,野心大, 力足,
力足, 险而诡诈。为了便
险而诡诈。为了便
于参考,并免于许多 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
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 名,以见双方之
名,以见双方之
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绍(两面 ,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与邓绍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雾(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 婿)
婿)
章谆(后为苏东坡敌 )
)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 )
)
曾公亮(脆弱 物)
物)
赵护
文彦伯(老好 )
)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 )
)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 火
火 ,东坡至
,东坡至 )
)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弟)
王安国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
宋敏求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 悲,又令
悲,又令 笑。一看此表,令
笑。一看此表,令 不禁纳闷王安石
不禁纳闷王安石
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
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绪等诸 。他的
。他的
强国梦 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
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 善任为“神”圣的降胜,
善任为“神”圣的降胜,
“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 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
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
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 的
的
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
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
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
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 。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
。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
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 ,无一不动
,无一不动 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
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
不能自拔的 ,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
,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 裂成了浮光
裂成了浮光
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 疏远起来,
疏远起来,
就连自己的莫逆之 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
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
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
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
“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 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 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 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 大恶的后盾
大恶的后盾 物,
物,
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 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
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 ,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 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 。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 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因为王安石本
,因为王安石本 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 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 事。
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此
 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回答说:“夫
回答说:“夫 吩咐
吩咐 婢伺候老爷。”
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回答道:“
回答道:“ 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 家丈夫卖掉
家丈夫卖掉 家好凑足钱数儿。”
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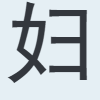
 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 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 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 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
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 不在,你胆敢
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 给弟兄
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 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 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 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 民
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 民将
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 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 。官方要做
。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 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 形,
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 发作相比,韩琦的
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 、功在国家的
、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 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 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
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 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 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 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 知利害,
知利害,
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 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 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 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 听的话说,
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 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 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 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 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 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 ,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 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 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 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 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
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 不服。吏受贿枉法,
不服。吏受贿枉法, 必谓
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 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 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 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 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 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 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 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 者,
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 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 之苦、鞭答之痛,
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 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 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 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 望,但是恶
望,但是恶 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
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 ,正如现代之专
,正如现代之专
制 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
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 为急务。
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 。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
。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 得
得 望。”
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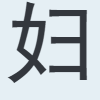
 ,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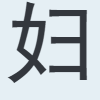
 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
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
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
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 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一被 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将此数 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 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
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 君子必败,而小
君子必败,而小 必占上风,因为
必占上风,因为
正 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
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 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
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 去位,坏
去位,坏
 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
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 矣。
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 。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 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 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 。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
。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 的朋友,都曾助他
的朋友,都曾助他
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

 躁又富有
躁又富有 才的孙觉,他也
才的孙觉,他也
是苏东坡毕生的友 ,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
,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
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 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
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
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 ,甚至在京辎一
,甚至在京辎一
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 事。王安石认为他这
事。王安石认为他这
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
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
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
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
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 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
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
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 。
。
在二
 好之
好之 ,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
,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
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 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
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
昭彰的小 进
进 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
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
史台引起了群 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
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 知
知
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 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
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
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
贷款法极受 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
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
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
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 一起丢官。其余的御
一起丢官。其余的御
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
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 古怪。只是听他叙
古怪。只是听他叙
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
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
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
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
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 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
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
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
很难为 。
。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
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 ,十一名是御史台的
,十一名是御史台的 ,三名是皇宫中的
,三名是皇宫中的
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 ,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 。“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
。“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 组织朝廷?就
组织朝廷?就
用这三个 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
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
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
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
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
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
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
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 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
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 之强,
之强,
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
陛下有 民之
民之 ,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
,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 与王安石看,
与王安石看,
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 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
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
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
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
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
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
所非。今 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
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
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
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
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
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 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
其个 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
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 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静清晰的推理, 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 ,
,
 隐忧,
隐忧,
因事而现。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
“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
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 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
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 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说:
书 :“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
:“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 主也。聚则为君
主也。聚则为君
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 各有心谓之独夫。
各有心谓之独夫。
由此观之, 主之所恃者,
主之所恃者, 心而已。
心而已。 心之于
心之于 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 主失
主失 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 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
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 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
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
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
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
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 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唯有 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
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 ,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不是 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 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 居其间,则
居其间,则
 君何缘知觉?
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 能比得上
能比得上
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
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 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 ,以致
,以致 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
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 物议沸腾,怨磋
物议沸腾,怨磋 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
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
内重之末,必有 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
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 方盛而虑衰,
方盛而虑衰,
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 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 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
 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 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
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 臣之始,以台谏
臣之始,以台谏
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 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
 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
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 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
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 俱增。
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 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恤于 言?夫
言?夫 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
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 必贪财也,而后
必贪财也,而后 疑其盗;
疑其盗;
 必好色也,而后
必好色也,而后 疑其
疑其 ……
……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
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 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
鹰大而赴林教,语
 “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
“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 罔答而
罔答而 江湖,
江湖,
语
 “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
“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 自信。
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
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
心,皇帝本 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
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
一个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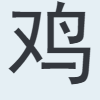 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
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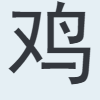 。后来使
。后来使 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
(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
小之辈会捏造藉 ,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
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 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
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
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 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 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
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 。陛下知道谢景温
。陛下知道谢景温
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
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
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
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
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记住网址 龙腾小说 ltxsba.com]
 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龙腾小说 ltxsba.com这场风
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龙腾小说 ltxsba.com这场风
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
 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
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
 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
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 质,因为
质,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
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
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
 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所知了。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
 个
个 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
 告诉我们,说个
告诉我们,说个 坚
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
 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
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 是用去做什
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
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
为
 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
 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
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 方面。他能言善
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
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
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
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
 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
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
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
 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
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
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
 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
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
 之
之 ”,也就
”,也就是使天下
 不得批评政府。
不得批评政府。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
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
的方法。中国
 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
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
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
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
 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
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
 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
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
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
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
 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
史台独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
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
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
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
 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
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
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
重臣
 练有才之士,
练有才之士, 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
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 ,王安石,
,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
 ,野心大,
,野心大, 力足,
力足, 险而诡诈。为了便
险而诡诈。为了便于参考,并免于许多
 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
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 名,以见双方之
名,以见双方之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绍(两面
 ,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舒曼(与邓绍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雾(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
 婿)
婿)章谆(后为苏东坡敌
 )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
 )
)曾公亮(脆弱
 物)
物)赵护
文彦伯(老好
 )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
 )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
 火
火 ,东坡至
,东坡至 )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弟)
王安国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
宋敏求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
 悲,又令
悲,又令 笑。一看此表,令
笑。一看此表,令 不禁纳闷王安石
不禁纳闷王安石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
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绪等诸
 。他的
。他的强国梦
 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
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 善任为“神”圣的降胜,
善任为“神”圣的降胜,“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
 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
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
 的
的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
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
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
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
 。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
。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
 ,无一不动
,无一不动 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
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
 ,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
,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 裂成了浮光
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
 疏远起来,
疏远起来,就连自己的莫逆之
 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
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
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
“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
 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
 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
 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
 大恶的后盾
大恶的后盾 物,
物,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
 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
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 ,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
 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
 。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
 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因为王安石本
,因为王安石本 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
 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传有暧昧
 事。
事。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此

 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怎么回事?”

 回答说:“夫
回答说:“夫 吩咐
吩咐 婢伺候老爷。”
婢伺候老爷。”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回答道:“
回答道:“ 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
 家丈夫卖掉
家丈夫卖掉 家好凑足钱数儿。”
家好凑足钱数儿。”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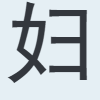
 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这种
 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
 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
 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
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 不在,你胆敢
不在,你胆敢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
 给弟兄
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
 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
 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
 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
 民
民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
 民将
民将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
 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
 。官方要做
。官方要做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
 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
 形,
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
 发作相比,韩琦的
发作相比,韩琦的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
 、功在国家的
、功在国家的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
 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
 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
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 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
 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
 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
 知利害,
知利害,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
 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
 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
 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
 听的话说,
听的话说,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
 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自己当然也
 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
 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打断,要他二
 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
 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
 ,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
 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
 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权力压制
 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
 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
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 不服。吏受贿枉法,
不服。吏受贿枉法, 必谓
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
 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
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
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
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
 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刑之说。他接着又说:“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
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
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
 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
 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
 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
 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
 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
 者,
者,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
 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
 之苦、鞭答之痛,
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
 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好弹劾
 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
 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
 望,但是恶
望,但是恶 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
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 ,正如现代之专
,正如现代之专制
 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
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 为急务。
为急务。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
 。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
。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
 得
得 望。”
望。”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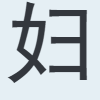
 ,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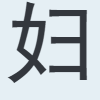
 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
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
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
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
 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一被
 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将此数
 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
 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
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
 君子必败,而小
君子必败,而小 必占上风,因为
必占上风,因为正
 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
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 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
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 去位,坏
去位,坏 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
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 矣。
矣。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
 。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
 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对当权者的意见,由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
 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
 。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
。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 的朋友,都曾助他
的朋友,都曾助他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


 躁又富有
躁又富有 才的孙觉,他也
才的孙觉,他也是苏东坡毕生的友
 ,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
,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
 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
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
 ,甚至在京辎一
,甚至在京辎一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
 事。王安石认为他这
事。王安石认为他这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
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
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
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
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
 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
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
 。
。在二

 好之
好之 ,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
,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
 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
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昭彰的小
 进
进 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
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史台引起了群
 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
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 知
知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
 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
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
贷款法极受
 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
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
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
 一起丢官。其余的御
一起丢官。其余的御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
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
 古怪。只是听他叙
古怪。只是听他叙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
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
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
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
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
 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
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
很难为
 。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
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
 ,十一名是御史台的
,十一名是御史台的 ,三名是皇宫中的
,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
 ,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
 。“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
。“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 组织朝廷?就
组织朝廷?就用这三个
 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
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
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
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
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
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
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
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
 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
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 之强,
之强,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
陛下有
 民之
民之 ,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
,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 与王安石看,
与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
 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
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
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
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
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
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
所非。今
 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
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
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
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
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
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
 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
其个
 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
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 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
 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
 ,
,
 隐忧,
隐忧,因事而现。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
“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
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
 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
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
 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说:
书
 :“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
:“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 主也。聚则为君
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
 各有心谓之独夫。
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
 主之所恃者,
主之所恃者, 心而已。
心而已。 心之于
心之于 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
 主失
主失 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
 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
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 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
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
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
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
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
 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唯有
 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
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 ,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
 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君的。苏东坡接着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
 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
 居其间,则
居其间,则 君何缘知觉?
君何缘知觉?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
 能比得上
能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
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
 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
 ,以致
,以致 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
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
 物议沸腾,怨磋
物议沸腾,怨磋 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
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
内重之末,必有
 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
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 方盛而虑衰,
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
 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
 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

 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
 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
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 臣之始,以台谏
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
 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
 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
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 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
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
 俱增。
俱增。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
 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
 言?夫
言?夫 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
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 必贪财也,而后
必贪财也,而后 疑其盗;
疑其盗; 必好色也,而后
必好色也,而后 疑其
疑其 ……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
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
 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
鹰大而赴林教,语

 “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
“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 罔答而
罔答而 江湖,
江湖,语

 “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
“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 自信。
自信。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
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
心,皇帝本
 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
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
一个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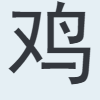 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
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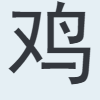 。后来使
。后来使 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
(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
小之辈会捏造藉
 ,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
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
 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
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
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
 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
 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
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 。陛下知道谢景温
。陛下知道谢景温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
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
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
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
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记住网址 龙腾小说 ltxsba.com]
最新地址:m.ltxsdz.com m.ltxsfb.com